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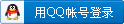
x
词曲:赵雷 图文/演唱:江华《少年锦时》是赵雷的一首歌,在《成都》最火的时候其实就听过,这两日偶然又听起这首歌,毫无征兆的一发不可收拾,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已然深度中毒。《少年锦时》没有浓妆艳抹,没有庸脂俗粉,一字一句,都是那么轻灵纯净、挠人心肺。不知何故,随着歌词,年少时的画面,一帧一幕,就那么清晰、生动地浮现在眼前,沉醉在记忆里,我甚至能感觉到眼角有一丝潮湿。

(我和弟弟)那时候的村庄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楼房,大都是五树三间的砖瓦房,有的还是泥砖房,感觉却比现在更有生机。每到饭点,就能看到家家户户炊烟袅袅,不多时就是母亲们的声声叫唤,在屋场各个角落、田野里撒欢的孩童们赶紧拍拍身上的尘土,跑回家吃饭了,偶尔也能看到顽皮的孩子,被母亲拿着鞭子追着跑的场景,母亲责骂着,孩子们依然是嘻哈欢笑。吃饭并没有说一定要围坐在家里饭桌旁,大人孩子都喜欢挺着碗,或到邻居家夹点菜,或聚集在村庄某一个角落边吃边聊,我已经记不得大人们聊的话题是什么了,但他们端着碗永远聊得那么起劲、开怀大笑的样子,却刻到了我脑子里!夏天的午后,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电扇,大人们摆好竹床,或者铺张凉席在贯风的巷道里,母亲倒也想拉上我和弟弟一起躺会儿,当然,那是拉不住的,中午是抓知了最好的时机。我们和小伙伴一起拿竹篙,在篙杪上绑一个塑料袋,留出一个小口子,听着声满村晃荡找树上的知了,套着了便用小绳子绑起来溜着玩,有些调皮的,把知了放到正在树底下纳凉的老人额头上,老人多半是佯打耳睁,蒲扇轻轻一拂,继续自摇竹椅,闭目养神,我们便也欢笑着跑去别处了。等不到日落,半下午时我们就钻到村里的水塘里去了。记得那时村里池塘里的水还很清澈,一头是洗菜(一般是洗头遍,回家再用井水清洗,井水是在村里为数不多的井里担回家的,得节约着用),另一头洗衣服,别问我这多不卫生啊,还得加上我们小孩天天在里面扑腾呢。池塘里有些玻璃瓦片,经常有伙伴割脚,割的血肉模糊还不敢声张,生怕父母责怪。大多数孩子就这么,在池塘里玩闹着,刨着呛着学会了游泳。至于我嘛,最终还是没学会,母亲向来不太让我们玩水,能偷偷趴在池塘边的洗衣青石板上刨刨已经算很不错了。到了晚上,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但无论春夏秋冬,不管严寒酷暑,我们从来不会窝在家里,也不缺乐子。村中央有个大晒场,那就是我们的乐园,老鹰抓小鸡、捉迷藏、踢房子、斗鸡……各种游戏轮番上阵,乐此不疲。说到电视,后来村里有一个伯伯买了台电视机,记得那时候电视剧《珍珠传奇》正热播,虽谈不上万人空巷,但晚饭过后,村里许多人便早早到那伯伯家占位置。让我印象深刻是有一回,看完电视回家,打开偏门锁进屋,发现大门居然没上栓,虚掩着的,父母亲为此还互相埋怨争吵了一番,都是珍珠给害的。

(年轻的父亲)小时候家里是真穷,田地少,产量也不高,无论父母亲怎么起早摸黑,辛苦耕作,粮食还是少。每到年后粮食就不不多了,新粮又还接不上,母亲便煮豆角饭,有时候是南瓜饭,那时候并不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难处。到了真无以为继的时候,母亲便会到外公外婆家找接济了。多年来,母亲就这么迎难克艰、勤巧持家,竭尽所能呵护着我和弟弟,所以年幼的我们并未感受到生活苦难,一直都在快乐、健康中成长!
除开父母亲,我能感受到爱意最富裕的地方,就是外婆家了。虽然小时候我对尊公(太外公)和外公很敬畏,甚至有些害怕,但有外婆永远如沐春风的宠爱,还有舅舅、姨娘们的疼爱有加,所以去外婆家当属最开心的事了。去外婆家不远,翻过一座石牛岭就到了,母亲怕我和弟弟爬山路辛苦,总是拿谷萝挑我们过岭,天冷的时候,怕我和弟弟冻着,母亲会在谷萝里放上棉布垫,垫子底下放一个装满热水的盐水瓶。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我和弟弟一人坐在一个谷萝里,母亲用扁担挑着我们,一步一步翻过石牛岭的场景,我甚至还记得爬石牛岭那个U字弯的时候,母亲一边淌汗,一边和我们谈笑的画面。
(做姑娘时的母亲,小姨哪里淘来的)在我的记忆里,尊公十分勤劳,八十岁都还上山砍柴,他清瘦的脸永远是那么严肃,吃饭的时候他总喜欢摆上两钱小酒盅,抿上两口,我们都不太敢靠近他坐,夹菜都是轻手轻脚的。尊公的房间我们也不敢迈进半步,但又十分神往,因为在他房间那个橱柜里,似乎总有拿不完的小吃,尊公最疼朋表弟,每次分东西吃,总是他先拿,那时候可嫉妒了。直到有一回,不知道是吃坏了东西还是着凉了,我上吐下泻,尊公着急的和外公都吵起来了,我深深知道,不苟言笑的尊公其实疼爱我们每一个小萝卜头,他是家族的大树,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藤,只是他爱得深沉。尊公去世之前去过一趟我家,在厨房走到大厅的时候,尊公被门槛绊到摔了一跤,那次尊公回家的时候,母亲沿着田埂一直送出很远,我看到母亲不知为何流眼泪了,母亲后来说,我们家门槛他平时很轻松从容,这次却没能过去,她预感尊公那次是来我们家辞路的,所以她的眼泪情不自禁就流出来了。尊公去世的时候,我也哭的很伤心,后来举行杠鸡祭事的时候,蒙着黑纱的筛子像通了人性,活灵活现的,我们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尊公一直都在护佑着我们这个大家族。
(外公外婆带着小姨的合影)外公那时候在偏远乡镇教书,不常在家,所以幼年记忆里并没有太多关于外公的故事,直到在外公和三舅那上初中,这是关于成长的另外一个故事了,浓墨重笔,容日后再叙。外公在外教书,家里的事全靠外婆张罗,外婆留在我幼时记忆里最深的,就是整天忙碌的身影,但无论怎么忙,外婆的脸色总是挂着笑容,看到外婆就犹如春风拂面。我们去了,更是嘘寒问暖,呵护备至,那种慈爱,让我们倍感温暖,流连忘返。而舅舅们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每年双抢的时候,都来帮忙,对我来说,双抢就像是过节,舅舅们来了热闹,饭菜比往常也会丰盛些。于我想,舅舅们对帮助他们的大姐搞双抢,不全是帮农活,慢慢也都成了一种情结,双抢这个情结,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姨娘吧 表兄妹一大家子)
说到小姨,我是要特别说说的。母亲姐弟妹七个,母亲排行老大,小姨老小,在母亲那一辈,小姨得到的宠爱应该是最多的,在我们眼里,小姨永远最漂亮,也最时尚。她的闺房在外婆房间对面,带地板的那种,房间总是那么干净整洁,墙壁上报纸贴的平平整整,还有漂亮的画报,各种小玩意,我们都喜欢到小姨房间玩。听小姨说,每次我想进她的房间总站在房门口问:姨,我能进来吗?我对自己在那么小的年纪,就那么彬彬有礼居然没印象了。小姨那房间早就没住人了,年久失修倒掉了,但就像小姨说过的,房屋倒了,房间依旧,安在心里呢。因为年龄相差不算太大,更多的时候,小姨更像是我们的大姐姐,农忙的时候,母亲没空管我们,她就常来负责看管我和弟弟,小姨曾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抱着我在老房子的后门等母亲回来的场景,对抱在手里时的事,我就更没印象了。不过在我读五年级时,家里开了个小店,小姨常常来帮忙我还是记忆犹新的,那是后话。
(猜猜我的小姨是谁)
(小姨的闺房)
那时候不像现在各种零食小吃琳琅满目,但我们也有自己的解馋之道。红薯长出的时候,我们随机在村后的地里刨起红薯,捡上干柴,然后在屋前就着田岸,上面凿个洞,侧面开凿与上面凿的洞连通,一个简易土灶就造好了,接下来就把红薯架在灶洞上方,侧面洞口放柴烧火,时不时用棍子翻动红薯,等烤得有点焦黑、香气喷喷时,顾不得烫手,就那么左右手腾挪开吃了,那个嘴烫的啊,只能不停倒吸冷气。吃完一抹嘴,才发现小伙伴都成了大黑脸,指着彼此笑到腰直不起来。每年蒜苗上市之后,母亲会一把一把的收集好,然后等人上门收购。大蒜也是如此,等收集到一定量了,父亲便和村里人结伴,挑去我不知道的地方卖掉,在那个年代,这都是添补家用的重要方式。虽然我总惦记吃蒜苗,却总难如愿以偿,穷啊,母亲虽不舍却也无可奈何。年幼的我并不知道这些,偶尔会在母亲收集好的蒜苗里,每把抽出一两根,掰成一小段一小段,然后放到洗干净了的小墨水瓶子里,再撒上一点盐,盖紧藏起来,等过几日,腌蒜苗便新鲜出炉了,那个味美啊,简直无与伦比。我惦记的还有大舅婆家门前几棵枣树。每年枣子快成熟的时候,我总时不时到大舅婆家门前溜达,幸运的时候,可以在树底下捡到枣子,那心情堪比当下福彩中奖。有一天下午我又溜达去了,看到大舅婆家关门了,估摸着是出去干农活了,看着满树的枣子,一下没忍住,找了跟棍子,敲下来一些,边吃边捡,突然大舅婆家门开了,我一时头脑空白,脚下却不听使唤直接走到大舅婆家了,然后居然还很冷静的告诉大舅婆,这是我刚在树底下捡到的枣子,给你收好了,放下枣子我转身就跑了。事后我也担心了好几天,生怕大舅婆告诉我母亲偷打枣子的事,那可不是小事,搞不好就是一顿打啊,善意的大舅婆没有戳穿我的谎言,并没有告诉我母亲。最开心就是大舅婆家打枣子了,我和弟弟都不请自来,热情帮忙,在枣树下帮忙捡的不亦乐乎,作为酬劳,最后我们都能得到大舅婆送的枣子,用衣服兜着枣子像是兜着一个个宝石,小心翼翼的生怕掉了一个。

(好像这照片后面是大舅婆家的枣树)过年前有两件我最期待的事,一件是打糖糕的,另一件是削过年猪(临过年忌说杀字,用xiao代替,权用削字顶岗,不一定准确)。过年时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糖糕,因为打糖糕需要用到一个大木框,这个木框好像村里只有一个,所以打糖糕需要提前挑好日子,确保能用到这个工具。到了打糖糕的那天,左右邻里帮忙的人都来了,母亲早早的就开始忙活了,厨房里大灶两口锅,靠里头那口锅熬制麦芽糖,外面一口锅就炒爆米、芝麻等。等火候到了,麦芽糖呈金黄色,用勺子拉起来那种丝滑特别诱人,我和弟弟总想尝一口,母亲怕我们被烫着,总赶我们到大厅去,我们禁不住又跑进去,母亲便把冷却好的小块拿给我和弟弟,这个糖黏乎、柔软、甜极了。等麦芽糖熬制好,冷却到一定程度就用铁勺舀到外面锅里拌爆米了,拌好一锅父亲就把它装进摆在大厅门板上的大木框里,不一会大木框便装满了,先盖上一层干净的布块,再覆盖上一层油纸,最上面铺上麻布袋,接下来欢腾的时刻到了,我们迫不及待的跳上去,开始和大人们一起踩糖糕,踩实了之后再压糖,等压实在了,掀掉覆盖,抬起大木框,一块四四方方的大糖糕制作好了,看着这么一大块糖糕,真想抠下一块来吃啊,父亲总会及时提醒我们莫心急,马上就切好能吃了。切糖糕堪称邻里伯母婶婶们的刀工大比拼,切的都那么快速齐整,这时候,我和弟弟终于可以收起口水,敞开吃了!削过年猪当然更是一件欢乐的事情。那会儿村里就只有两位年长些的伯伯专职削猪,同样需要预约,因为削猪用的大盆也只有一个。母亲照例是最先忙活起来的,早早的要烧好一大锅开水,水烧开了还要继续加柴火,保证开水一直沸腾着。水开了之后,父亲便和伯伯们一起到猪圈,用系在扁担上的绳索套猪脖子,等绳索圈住猪脖,轻轻撤下扁担,迅速收紧绳索,这时猪已经逃不开了,只能不停地挣扎嚎叫着。随后伯伯拉绳索往前拖,父亲抓住猪尾巴的往前推,众人七手八脚的把猪脖搁到跨在猪盆的板凳上,这个时候,摁猪后腿的是最危险的,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踢着,按稳后,伯伯一手压住猪头,一手拿起锋利的尖刀,对着猪脖子,手起刀落,鲜血就喷出来了,伯伯大喊打开水来,一边用刀柄划拉着猪血。待猪血端开,两大桶热气腾腾的开水倒进大猪盆,开水浸泡年猪时,一直远远看着的我这才走近来了。泡的差不多就开始去毛,这是细致活,等两位伯伯耐心去完之后,用一个铁钩勾在猪后腿上,挂到楼梯上竖起来,开膛分离处理猪内脏。那时候我最关心的是猪尿泡,很多小伙伴都有用猪尿泡做的气球,怎么玩怎么摔都不会破,特别羡慕,但遗憾的是,记忆中我一直都没能得到那个猪尿泡气球。说到遗憾,还有夏天那美味的冰棍。每到天热,只要听到屋场有人叫唤卖冰棍咯,我就立即寻声找去了,于是就看到一群小孩子跟在一辆自行车后面,车架上拖着个木箱子,有人买的时候,我们的小脑袋都凑上去了,只见打开箱盖,掀开一层旧棉衣,再打开一层泡沫,一箱冰棍映入眼帘,看着那纸包的冰棍,每个人都忍不住口水直吞。虽然只要一角钱,或者用旧的解放鞋底、凉鞋底也可以换,但那时候,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找不着钱,也找不到一只旧鞋底,所以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冰棍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不过冬天的时候,我们有个弥补遗憾的机会。小时候的冬天好像比现在冷多了,每到冰雪天,伴随着融雪,常常是打冻天,清晨起来,总能看到屋檐下的瓦弦上,吊着一排长长短短的凌水钻(冰凌),我们总爬到相对较矮的偏房屋檐下去取凌水钻,大冬天的就那么拿在手里嚼上了,这可是免费的冰棍啊。过年前父亲会采购些年货,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弋阳香槟了。有一年,父亲照例买了一扎弋阳香槟,放在房间床底下,我天天盼过年,天天跑去看看那香槟,终于有一天没忍住,偷偷撬开了一瓶,也没拿出来,趴在地上就着瓶子喝了几口,又把瓶盖轻轻盖上了。就那么每天偷偷喝上几口,到过年的前一天,香槟被我喝了个瓶见底,眼看就要穿帮了,我灵机一动,拿母亲洗衣服用的木衣锤轻轻敲打瓶盖,瓶盖居然被我敲的严丝合缝。过年那天,父亲从床底下搬出香槟的那一刻,我内心是忐忑的,不知父亲是真没看出来,还是故意放过,看到那香槟酒空瓶子,只听他说了句,怎么买到了一瓶空酒,听到父亲那话,我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关于过年,记忆中除了热闹还是热闹。我们村里一直沿袭着每年最后两天过两个年的习俗,过年那天傍晚,每家每户端着木盆到村里的祠堂集中,木盆里放着猪头和一些祭品,等全村老少都到齐整了,摊开鞭炮,祭拜完毕,祠堂里敲钟人一声令下,伴随着声声钟响,顿时鞭炮齐鸣,响声震天。放鞭炮像是比赛,村里年景好一些的,都会尽量买大一点的鞭炮,放到最后,大家都在看他家的鞭炮响了,等鞭炮响完钟声才停,大家也才能各回各家,开始吃年饭。吃过饭,我们就跑去各个家门口找掉落了的、引线还在的鞭炮,收集起来,拿上一根香,时不时放上一个,偶尔看到小伙伴点燃引线丢得不及时,炸到手了,疼得龇牙咧齿,我们笑的手舞足蹈,摇头晃脑。正月十五闹元宵,村里年长的老人,早早的就用稻干扎好大大小小的龙,用木棍撑着,等到天黑,在龙背上插上香,锣鼓一响,我们就跟着大人们,开始游灯了。游灯又叫赶散(大致意思是驱赶野兽,驱走霉运之类),村前屋后,山上地里,水坝田埂,都要走个遍,开始我还能跟得上,但毕竟年小,总是跟着跟着就掉队了。有一年元宵夜下雨,在村后山上,我又掉队了,天黑找不着路,举着龙灯吓得直哭,老半天听到母亲喊我,是母亲上山找我来了,那一回把自己吓坏了,也把母亲吓得够呛。赶完散,大人们就开始在家里打牌消遣,同时也是守着不让邻村的下马灯丢到我们村这边来,这可不是小事,搞不好是要打群架的。我们小孩子就举着小龙灯,在村子里串门,每到一家,都要放鞭炮迎接我们,我是负责掌彩的,是奶奶教我的,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每掌一句,同行的伙伴就喝上一句好啊,掌完彩,每家都会拿一些烟、糕点或者面条。全村走下来,我们就在祠堂里集中,开始分烟分糕点,见者有份,每个人都是乐乐呵呵的,面条总是拿到村上头一位伯伯家煮来吃,几乎全村的小孩都没有睡觉,就等着这大半夜的一小碗面,太美味了!

(年轻时的母亲)
小学一到三年级,我们都在村里面上学,父亲是村里唯一的老师,他一个人负责三个年级的所有课程,而且我们都在一个教室里,很难想象,父亲是怎么把我们带出来的。到了四年级,我开始离开父母亲,到相隔一段路程的邻村铺里小学上学了。在铺里上学后,不像在村里那么方便,在家里天冷了母亲会提前搞好火桶,让父亲带着去学校。不过我却由此学到了一个新的取暖方法:找一个废旧的铁罐,用铁钉在铁罐底钻上密密麻麻的小孔,用铁丝做提手,取火工具就做好了。接下来就是在铁罐里加一些晌炭,取一个火种放到晌炭里,用塑料笔筒对着吹气,再提着铁罐,360°循环甩臂,铁罐里的炭火很快就燃起来了,既可以暖手,也能在铁罐口烤脚,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没把握好,对着吹气的时候,容易呛着灰,甚至让晌炭搞到满脸黑。五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住校,记得我们男生是住在二楼地板上,二楼有一点方便,就是谁尿床了,被子直接搂到阳台就可以晾晒了。还有一个方便的地方是后来发现的,那时候《雪山飞狐》电视剧正热播,每天晚上快播出时,值日老师把我们赶到楼上,锁好门,麻溜的去小学旁边的村民家看电视去了。当隔壁传来“寒风潇潇,飞雪飘零,长途漫漫踏歌而行……”的主题曲时,我们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下去了,突然有一位同学发现,齐楼板有一处窗户上面的摇头露出来了,打开那摇头小玻璃门,令我们惊喜的是,窗户摇头这居然没有钢筋,于是我们排着队从窗户摇头小门钻出去,更令我们惊奇的是,窗户外面居然是村民家的猪圈,盖的真不是地方啊,顾不上踩在猪圈里的脏臭,我们翻身而出,挨户敲开正播放《雪山飞狐》村民的家门,很多人一看是我们,赶紧又把门关上了,最后终于找着一位好心的村民,勇敢地收留我们了。故事到此结束了?并没有,看完电视,我们飞速从猪圈原路爬回二楼,惊讶的发现,前面上来的同学一字排开,笔挺的站着,我正迟疑呢,没出去看电视躺被窝里的同学悠悠地说了句:老师让你们站好等他。我顿时没脾气跟着站上了。不多时,我们听见值日老师开锁的声音,上楼一抬头,看见我们站那,我确定他的眼神里,有疑惑,有讶异,甚至还有些惊吓,但很快老师就整理好情绪了,一脸严肃的问我们干嘛都站着,也不知是哪个嘴快的同学,赶紧回了句,不是你叫我们站吗,我们刚看电视回来呢。这时候我听到被窝里传来压着的阵阵笑声,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再见,年轻时的我)
原本,我只是想写一点《少年锦时》听后随感,不曾想,记忆就像是洪流一般,闸门一开,就怎么也收不住了,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个止于小学的时间节点,后面的故事,留待以后再讲述吧。感谢《少年锦时》,唤醒了我年少那段沉睡已久的记忆,给我带来了纯粹的欢笑和泪水。这些画面,虽零碎,却真实!青春是一场远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总能在其中找到似曾相识的场景,或多或少,这,就足够了。以上,献给我们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这是后来的故事........
附:《少年锦时》歌词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
凌晨的集市人不多
小孩在门前唱着歌
阳光它照暖了西河
柳絮乘着大风追
树影下的人想睡
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
脱掉寒冬的傀儡
我忧郁的白衬衫
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
情窦初开的我
从不敢和你说
仅有辆进城的公车
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
晴朗蓝天下 昂头的笑脸
爱很简单
钟声敲响了日落
柏油路跃过山坡
一直通向北方的 使我们想象
长大后也未曾经过
扒满青藤的房子
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
秋天的时候 柿子树一熟
够我们吃很久
收音机靠坐在床头
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
陪我入睡的 是月亮的忧愁
和装满幻梦的枕头 沾满口水的枕头 我忧郁的白衬衫
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
情窦初开的我
从不敢和你说
仅有辆进城的公车
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
晴朗蓝天下 昂头的笑脸
爱很简单……
|